作者: 曾德雄
贾谊是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公元前200年生于洛阳,也就是刘邦称帝后的第三年。文帝时任博士,李商隐那句著名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文帝向贾谊问策的事。《新书》是贾谊的政论文集,“过秦论”是其中的名篇。我原先一直以为“过秦论”是他经过秦国旧址时发的感慨,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论秦之过”的意思,总结、反思秦二世而亡的过失,主要是说秦严刑峻法,不够爱民(“仁心不施而攻守异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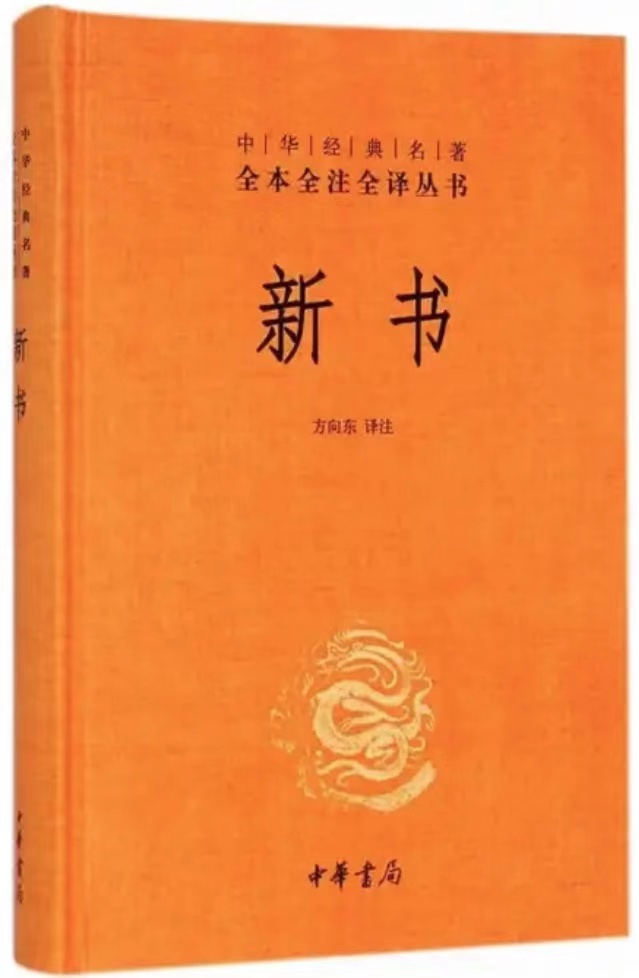
《新书》可谓是一本儒家人治教科书。这包含几层意思: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终极关心的都是政治;他们心目中的政治都是人治,区别只在于方法手段不同(法家其实也是人治,以后有机会再说);《新书》的思想是儒家的人治。因为贾谊做过长沙王和梁怀王的太傅(辅弼官,君王年幼时充当老师),所以可以看作是一本儒家人治教科书。
儒家的人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度的集权,二是最高的德行,在儒家的思想逻辑中这两者缺一不可且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德行就是儒家心心念念的“仁”,在人君或皇帝身上就是“爱民”,德是爱民之心,行是爱民之行。有了这样的德行,就会达到如贾谊所说的“帝之威德,内行外信(伸),四方悦服”的天下大治。
集权在贾谊生活的年代依然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严重问题。秦始皇开创了“定于一尊”的皇权专制,但二世而亡,仅仅存续了十五六年。项羽分封天下显示了历史的强大惯性,虽然项羽个人魅力千古闪耀,但毕竟与时代潮流不符,很快就灭亡了。刘邦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历史的惯性,一方面自己当皇帝,同时还分封了很多诸侯王(可参看李开元先生的《秦崩》《楚亡》《汉兴》)。经过高祖刘邦、惠帝、吕后的不断剿灭杀戮,到文帝时期诸侯王势力虽然较之从前削弱了很多,但依然尾大不掉,成为帝国的巨大隐患。
贾谊花了很多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基本上《新书》第一卷说的都是这,最典型的是“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等篇章,“陛下何不一令臣熟数(一一详细分析说明)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陛下试择焉?”贾谊的基本观点,首先是人主之尊,应该做到“尊不可及”,如此才能号令指使天下百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领袖挥手人民前进的意思。但当时的情形却是诸侯王势力依旧强大,“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以致贾谊反复说这样的形势如“倒悬”,非常危险,令人“痛惜”、“流涕”、“长太息”。贾谊的建议是“众建诸侯”:“其有子,以国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须(系?)之,子生而立。……子子孙孙与汉相须,皆如长沙可以久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义,国小则无邪心。”也就是将诸侯国的封地不断地分封给诸侯王的子孙,子孙越来越多,封国也就越来越小了,这样就不至于对汉帝国造成威胁了。为什么不干脆一劳永逸地废除这种分封制呢?我们只能说在当时,历史的惯性遗绪仍然留存,整个社会还没有想到这一步,连贾谊这样有超前眼光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脑洞大开到废除分封制的程度。
集权之后是爱民。爱民是儒家一贯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如孔子所说:“古之为政,爱人(民)为大。”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贾谊也反复劝喻君王要爱民,主要集中在《大政》、《修政》等篇章中。按他的说法,“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这是典型的先秦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他还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这显然是他当诸侯王太傅时说的。贾谊将爱民提到为政之要的高度:“德莫高于博爱人(民),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民)。”“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如何爱民呢?“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身处地、急群众之所急的意思。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做到“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恩德广博,教化鸿富)。”“故不赏而民劝(忠心、服从),不罚而民治。”显然这是典型的儒家人治思路。
为什么要爱民?贾谊当然不可能有“权利让渡”这样的现代法治理念(政府的全部权力来自公众的授权,成立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公众服务),也还没有像后来的董仲舒等人那样,以爱民为道德核心构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目的是论证刘邦布衣君相的正当性)。贾谊更多地是从巩固权力的角度来说明必须爱民:“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似乎在他看来民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民多力而不可适(敌)。”“民不可不畏。”这跟一千多年以后的载舟覆舟之说一脉相通。
在他心目中,民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原来既不是“爱民如子”的亲族家人,也不是诸如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勤劳勇敢、创造历史啥的人,而是至贱至愚:“夫民之为言也,暝(昏暗)也;萌(氓,指老百姓)之为言也,盲也。”“故民者,积愚也(人民就是汇集在一起的愚人)。”这样的观点被后来的经学家、纬学家全盘接受,比如董仲舒就说:“民者,瞑也。”“性而瞑之未觉,天所为也。效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纬书《孝经援神契》也说:“民者,冥也。” 冥、暝、瞑,都指昏暗无光、目盲无知,可见这是当时的普遍思潮,事实上在专制极权眼中,民就是至贱至愚的。
面对这样的民,应该怎么管治呢?贾谊的观点是教化:“民至贱不可简(怠慢),至愚不可欺。”“虽有不肖民,化而则之(教化使他们守规矩)。”“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上率下。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上下通顺、天下大治:“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人君发令如同发声,民众学习响应如同回声),曲折而从君,其如景(影)矣。”这显然是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进一步深入阐释。这也是儒家跟法家最大的不同:两家都认为民众至贱至愚,儒家主张教化,而法家采取的手段是威逼利诱、严刑峻法,而在实际政治中,则是如汉宣帝所说“霸王道杂之”,也就是所谓“儒表法里”,按董仲舒的说法就是:“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我一直认为这才是儒家人治(德治)的精髓。
总之,在贾谊看来,民至贱至愚(“积愚”),但因为人多力量大(“民多力不可敌”),“不可不畏”,必须爱民:“民者,弗爱则弗附(不爱就不拥护你)。”“民之不善,失之者吏也。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这一切都有赖于君主圣明选择良吏:“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正因为民、吏、君的关系如此密切,贾谊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建的思想:“吏以爱民为忠。”也就是说,对皇帝的忠诚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通过爱民来体现的,如果不爱民,导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就是不忠君,就是不维护皇帝的权威地位。
贾谊甚至提出皇帝应该以民的好恶为标准来决定吏的去留:“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称赞)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归附)而举(提拔)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见非(过错)而去(免职)之。”“故王者取吏不妄(随意),必使民唱(同意),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标准)也,察吏于民,然后随(顺应)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归附),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也就是说有多少人爱并且归附于他,他就当多少人的官。
贾谊的这种美好愿望当然是“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它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经不起人性针尖的轻轻一戳,实际政治发生的无不是“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当然我们决不能苛责贾谊没有民主觉悟,民主传入中国也才一两百年而已,其精义现在都还没有被我们真正理解、接受,何况两千多年前的贾谊呢。
《新书》里面有一篇“容经”,专门讲视听言动、坐卧起行的各种姿势,其中的“跪容”特别有意思:“跪以微磐之容,揄右而下,进左而起,手有抑扬,各尊其纪(跪下时身体微微前倾,右脚滑地跪下,左脚向前起身,两手各有高低,手脚各自遵守动作的规定)。”这实际上讲的是古人跪坐(正坐)的姿势。我们现在的这种坐在凳子上双脚垂直着地的坐法(胡坐)是南北朝以后才从西域传入的,到宋代才正式取代了跪坐(正坐)。贾谊的这篇“跪容”并不是在教奴才怎样下跪,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2021年12月3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