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德雄
荀子是赵国人(首都邯郸),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比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晚两百多年,比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晚五十多年,两人居然身处同一时空二十多年,但似乎没有任何“线下”交集。比他的学生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大三十多岁,另一位学生李斯生年不详,荀子不知大他多少。荀子卒于公元前238年,死后十七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荀子本名况,字卿(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后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而改叫孙卿。但汉宣帝字次卿,难道叫孙卿就不用避讳了么?历史也许有很多细节谜团永远消失在时光隧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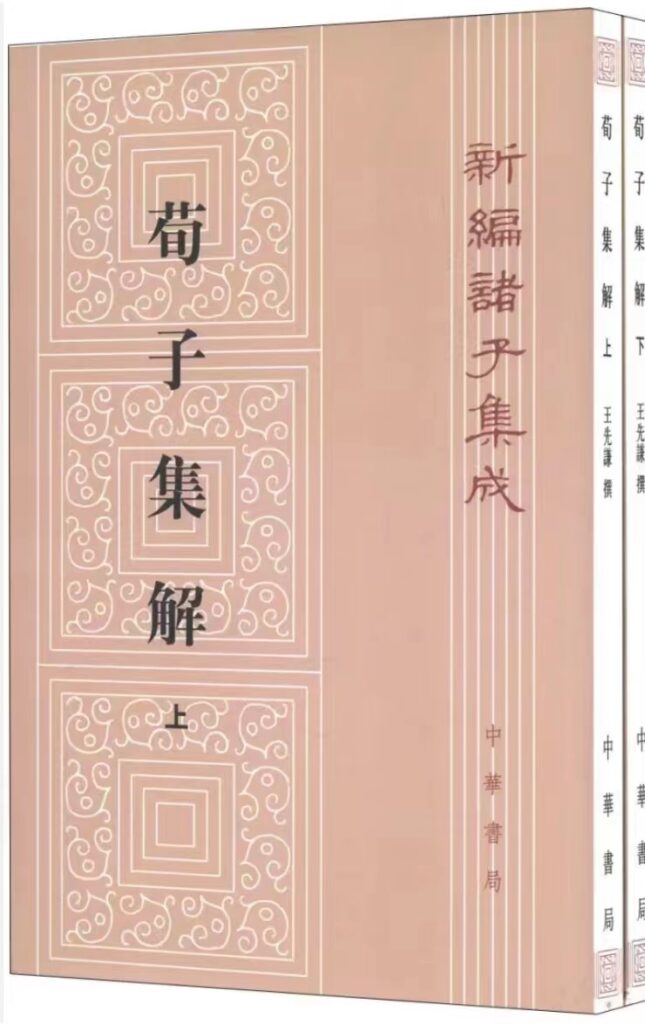
荀子最有名的观点是“性恶”,《荀子》第二十三章就专讲“性恶”,按他的说法,“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引自《性恶篇》,以下所引如不特别注明均引自此篇。)“伪”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人为”的意思,就是说人性本恶,所谓善都是后天人为的结果。
被他称作“恶”的人性是什么呢?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贪婪、懒惰、淫荡等等。如果顺着这些(恶的人性),那么就会天下大乱:“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无)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分”是个常见的古代政治概念,一般指个体、个体的边界)乱理(情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由)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人性本恶,必须要靠人为的努力来修正、规制它,这就是荀子的基本逻辑:“故枸木必将待檃栝(檃栝,yǐn kuò,矫正木材弯曲的器具)、烝(蒸)、矫(矫正)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砻砺,lóng lì,磨刀石,引申为磨练、切磋)然后利。”这样的比喻在《荀子》中很多见,都是为了说明通过(后天)人为的努力来改变(先天)恶的人性,使之向善。对于这个过程,荀子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化性起伪”。
“化性起伪”的是圣人:“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圣人通过礼仪、法度来“扰化”人的情性并加以引导,目的是为了天下大治、合于正道。
但问题是既然人性本恶,礼仪从何而生?“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怎么)生?’”荀子的回答是礼仪不是产生于“圣人之性”,而是来自于“圣人之伪”:“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shān zhí,和泥制作陶器)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工人斲(zhuó,砍,削)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后天长期的自我修为)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将“圣人之性”与“圣人之伪”分为两物,礼仪法度这些驱人向善的东西来自于“圣人之伪”,而不是来自于“圣人之性”。
先不论“圣人之性”与“圣人之伪”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以及两者能否并列,荀子在这里倒是提出了两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是圣人的人性是恶还是善?二是如果圣人的人性也是恶的,他凭什么可以“化性起伪”?
关于第一个问题,荀子认为圣人的人性也是恶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盗跖:dào zhí,盗贼或盗魁,泛指品行恶劣之人),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品行高尚和品行低下的人、君子与小人,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这样的观点贯穿荀子的整个思想:“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篇》)
之所以品行有高下,有人为君子有人为小人,只在于君子能“化性起伪”,而小人不行:“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孳,以出乎贪利争夺。”
为什么君子能“化性起伪”而小人不能呢?荀子认为“非不能,实不为”:“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而涂(途,路途上的人,泛指普罗大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悬)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具备知晓“仁义法正”的质地、做到“仁义法正”的工具,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圣人。之所以没有人人成圣,在于“可以而不可使”,也就是我们说的“非不能,实不为”,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去做。他还打了个比喻加以说明:“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遍行天下者也。”人人都有脚,但有人遍行天下,有人却足不出户,区别就在于前者“有为”,而后者“不为”。
除了这些主观的因素,荀子似乎认为还有客观的原因:“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埶(yì,shì,至尊权力)注错(措施)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不同的权力形态导致不同的习俗,长期积累下来,于是有的人成为君子,有的人成为小人。
君子“化性起伪”,首先是“化”自己的“性”,让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然后“化”天下人之“性”,最终使天下臻于大治:“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统一天下于礼仪法度)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礼论篇》)这就又是典型的中国人治思想了:“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带领、统领)人者之大本也。”(《强国篇》)
类似的表述在荀子那里非常多,比如:“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须,发生关联)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跟没有君王一样)!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que,四声,诚恳)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上周密(忌讳频密,严密监控),则下疑玄(疑惑丛生,指思想不统一)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正论篇》)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以上率下的意思。
以上率下的前提是“上”要“正”,如何确保“上”“正”?以什么标准来评判“上”“正”还是不“正”?由谁来评判?荀子说“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正名篇》),由谁来决定什么是正道什么不是正道?这些荀子并没有明说,他甚至认为这些根本就无需“辨说”,否则就是“饰邪营众”,应该杀头:“夫民易(容易)一以道(统一于道),而不可与共(不可与共事,类似于商鞅说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故。”“故明君临之以埶,道(导)之以道,申之以命,章(彰)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哪里还需要辨说)!”“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正名篇》)
这其实是中国统治者一贯的主张,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民众只需要服从听从顺服就行了,别问这问那说这说那。因此之故,荀子对孔子“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是大加赞赏的,他借孔子的话说:“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吸引、鼓动民众),强足以反是(政治正确,类似于‘国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宥坐篇》)
孟子道“性善”,荀子讲“性恶”,这是孟荀最大的不同。荀子在《性恶篇》中专门批驳了孟子的“性善”论,说孟子“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他进一步举例说明:“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由)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显然荀子心目中的人性指的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而“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劳而不敢求息者”这些礼仪法度,这些人的社会性在荀子看来不属于人性的范畴,而属于后天的“化性起伪”,对人性的“扰化”,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性的克制、修为、引导。
孟子主张“性善”,目的是为了论证圣人的存在,为圣人的存在提供一个形上的依据,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才有圣人存在,所以他特别强调“反求诸己”、“放心”,都是劝喻人回归(善的)本性。荀子同样认为圣人是存在的,但认为圣人并不来自于天生,而来自于后天的努力(“积伪”,长期的自我修炼),人要做的不是回归本性,恰恰相反,是“化性起伪”,改变(“扰化”)先天(恶)的本性,在这点上他跟孟子的观点完全相反。
从历史效应来看,显然孟子的观点占了上风,除了更具逻辑的思辨力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哪一个自称天纵英才的伟人圣人认为自己跟普罗大众一样人性本恶,否则的话,“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正论篇》)的“定于一尊”的合法性依据就不足了,也严重影响了“道德纯备,智惠甚明”(《正论篇》)的伟人成色。
但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以德主治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都是一样的,所以荀子反复说“明主谲(决)德而序位”(《儒效篇》)、“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正论篇》),其结果当然不是人人向善个个争先,反而是“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大略篇》)层出不穷,这可能是孟、荀诸人完全没想到的吧。
荀子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观点,认为人性险恶,必须要有一个圣人来统领天下,“替天行道”、“代天理物”,否则就会天下大乱。经过了这么多苦难和试错,我们现在终于意识到,“使天下出于治、合于善”的“埶”只可能是民主,而不是任何天纵英才、丰功伟绩、“定于一尊”的什么圣人。
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
作者:曾德雄(现为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