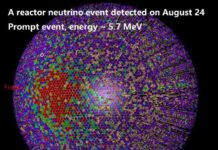中新社成都11月5日電 題:孔子與蘇格拉底如何影響東西方哲學的“底色”?
——專訪四川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教授熊林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兩千多年前的“軸心時代”,孔子與蘇格拉底地處歐亞大陸兩端,共同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如果蘇格拉底遇見孔子,他們會有怎樣的對話?”是海外社交媒體上一個有趣的話題。希臘學者赫里斯托斯·卡夫德拉尼斯甚至著有《當蘇格拉底遇上孔子:希臘與中國思想家的跨時空對話》一書。
孔子與蘇格拉底有何共通之處?二者如何深遠影響了東西方哲學的“底色”?對古典學經典作品的翻譯、研究,如何促進東西方文明互鑒?受邀出席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四川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希漢對照《柏拉圖全集》譯者熊林教授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哲學起源於何時,其本質是什麼?在“哲學”一詞傳入中國前,中國有哲學嗎?
熊林:Philosophy(哲學)的前半部分“Philo”意為熱愛,後半部分“sophy”意為智慧。據說第一次使用這個詞語的人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畢達哥拉斯認為,唯有神才是智慧的,而人祗能是追求智慧,熱愛智慧。
在希臘,哲學經歷了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問“這個世界從哪裡來,我從哪裡來”,我們將其稱為宇宙論。另一個階段是由巴門尼德等發端,到蘇格拉底形成的一種思考和發問方式,即問“是什麼,是怎樣”,以及對這種思考和發問方式自身的思考。
漢語原本並無“哲學”一詞,祗有“哲”“學”二字。19世紀晚期,日本學者西周經過思考和取捨,最終將philosophy一詞譯為“哲學”。後來“哲學”一詞傳入中國,沿用至今。
哲學一詞傳入中國時,人們理所應當地認為中國也有哲學,並將中國傳統思想以一種哲學的方式進行梳理、解讀和討論,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等。但也有人質疑古代中國是否真的有哲學。一種觀念就認為,既然哲學一詞是舶來詞,那麼這一詞傳入中國前,中國無哲學。
事實上,一種觀念由誰提出來、來自哪裡,與這種觀念所具有的內容和蘊含的意義是兩回事。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擁抱這種觀念,它成不成為我們自身生活的一部分。
祗要今天中國人以一種哲學的方式進行思考,那中國就是有哲學的。祗要我們用一種哲學的方法和精神去看中國歷史上的經典,那麼這些經典在我們的視野中就會以哲學的方式顯現。
中新社記者:同為“軸心時代”東西方偉大的思想家,孔子與蘇格拉底有何共通之處?
熊林: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了“軸心時代”這一說法,用以指稱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文化突破現象。
“軸心時代”的古希臘哲學三賢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人們也常常把他們同中國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進行類比。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蘇格拉底也沒有留下自己撰寫的作品。孔子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孔子門人及再傳弟子集結成的《論語》中。蘇格拉底的思想也主要記載于柏拉圖筆下以蘇格拉底為主人公的對話中。
孔子與蘇格拉底都是自身思想的實踐者,而非單純的理論家。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形容自己“纍纍若(如)喪家之犬(狗)”,那是因為孔子希望能踐行自己的思想、實現自己的理想。蘇格拉底更是在實踐自己思想的過程中坦然赴死。
中新社記者:孔子與蘇格拉底如何影響東西方哲學的“底色”?
熊林:雖然亞裡士多德說蘇格拉底是第一個“尋求普遍”和“試圖下定義”的人,但羅馬的西塞羅則認為,蘇格拉底首先把哲學從天上召喚到人間,迫使哲學思考個人和城邦的善與惡。後一種評價,實際上是說蘇格拉底將早期哲學家對自然的關注,轉為了對人的生活和社會的關注,也可以理解為從早期的自然哲學轉向了實踐哲學。
而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進一步發展了蘇格拉底的思想。所以有觀點認為“整個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思想的註腳”。柏拉圖的弟子亞裡士多德更是在西方成了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們三人所開啟的理性主義的道路,深刻影響了後來的西方哲學。
中國哲學一開始就更偏重於倫理學和實踐哲學,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表示,先秦諸子百家雖然各有不同,但是目的都是為了“治”,為了國家的治理、為了社會的治理,當然也包括對人的治理。
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啟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定下了儒家的基調,注重對人精神層面的反思,以及對由人所構成的社會的反思。
中新社記者:您從2018年開始重譯《柏拉圖全集》,目前已進展到哪一步?對古典學經典作品的翻譯、研究,如何促進東西方文明互鑒?
熊林:從19世紀開始,德語世界、英語世界、法語世界等著手系統整理柏拉圖的古希臘文原著,並將之譯為相應的現代語言,出版了大量的單行本和全集本。早在清末民國初年,中國學者就開始譯介柏拉圖的作品。
2018年受中國商務印書館所邀,我計劃用十年時間,以權威精校的古希臘文本(牛津古典本)為底本,翻譯出版希漢對照的《柏拉圖全集》。希漢對照《柏拉圖全集》涵蓋柏拉圖現存所有作品,包括九個四聯劇(36部)和一部偽作。
6年過去,我已經完成並交稿23部柏拉圖的作品,出版了16部17册。但現在看來,要完成《柏拉圖全集》的翻譯,十年時間肯定不够。翻譯不祗是語言的轉換,而是攜帶自己的世界,與作者的世界進行相遇,是情感的投入和一定意義上的生命交付,體現著譯者的創造性。
翻譯《柏拉圖全集》不僅要看希臘文原文,還要參考、利用過去兩百多年來全世界多個語種對柏拉圖作品的翻譯、研究成果。除了西方對柏拉圖著作的編輯校勘在推進之外,東西方不同時代的譯者對柏拉圖作品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最後他們訴諸自己的文字、表達成的思想也有所不同。而這些作品本身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見證與縮影。
不僅西方的經典會不斷被翻譯為中文,中國的經典也會被一代又一代西方學者翻譯成不同語言的著作。因為經典是經歷了思想、時間洗禮過的作品,祗有瞭解文明的源頭,才能更好瞭解今天不同的文明。
從哲學的角度看,唯有人是有歷史的,因為唯有人是向著未來籌劃自己的生活的。人類要朝著未來走去,所以人類的過往才會成為一面鏡子。我們重視古典學,是因為我們重視世界文明的源頭。這也讓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一場讓東西方回到文明源頭進行互鑒的對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