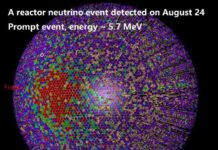中新社舊金山9月22日電 題:如何從“功夫”角度詮釋儒家思想?
——專訪美國格蘭谷州立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倪培民
中新社記者 劉關關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哲學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了貢獻。儒家思想也可從“功夫”的角度詮釋。怎樣幫助西方人更好理解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如何更好地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美國格蘭谷州立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倪培民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上述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請談談您的哲學學習和研究之路。
倪培民:我最初進入哲學領域可說是“為生活所迫”。小學五年級時,“文革”開始,社會的動蕩和家庭受到的衝擊,使我陷入迷茫。中學畢業後,我在工作中因高壓觸電雙手致殘,差點丟了性命,使我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上下求索”。幸運的是,那時我有緣結識了曾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後來成為上海《社會科學》雜誌主編的劉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導下,我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所有能到手的哲學著作,做了大量筆記、卡片。恢復高考後,我報考的志願選項裡,全都是“哲學”。
我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候,用功最多的,除了馬克思主義,便是古希臘和近代西歐哲學,因為古希臘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而近代西歐是世界進入現代的轉折點,我希望於此尋找擺脫困惑的思想資源。
有意思的是,我是在去美國留學後才重新“發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當代價值。我的博士學位導師柯普曼(Joel J. Kupperman)教授對東方哲學有濃厚的興趣。在我讀博期間,他先讓我在他的東方哲學課程裡擔任助教,接下來又要求我獨立給美國的本科生講授中國哲學。這就迫使我重新認真閱讀《論語》《孟子》《道德經》《莊子》《壇經》等中華經典,思考如何用英語準確地表達其含義。這個過程使我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智慧有了全新的感受。也逐漸走上了中西比較哲學的道路。後來我發現,與我同時代出國學習哲學的人,幾乎都先後轉向了中西比較哲學。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中新社記者:如何從“功夫”角度詮釋儒家思想?通過“功夫”,您的西方學生是否更容易接受儒家思想?
倪培民:我認為儒學本質上是一個功夫體系,我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也確實以從“功夫”的角度來系統地詮釋儒家思想為主。相比於當今流行的其他詮釋框架,如心性儒學、政治儒學、生活儒學、自由儒學、情感儒學、進步儒學等,我認為“功夫”更準確抓住了儒學的核心,也更能統合儒學本身的各個維度。祗是我所做的不祗是提供一種對儒學的詮釋,也是一種功夫哲學的建構。
由於武打電影在世界普及,“功夫”這個詞可說是世人皆知。我把“功夫”定義為“生活的藝術”。在中國傳統哲學裡,功夫通常被用來特指有關心性修煉的學問。但在日常用語乃至儒學中,它也不僅僅是指心性的修煉,而是泛指各種生活的藝術。作為生活的藝術,功夫的實踐和對它的思考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不祗中國才有,但對生活藝術的追求是中國傳統思想關注的核心。功夫不是可單純“採用”的方法或者“遵循”的道,它要求主體進行修煉踐行,成為具備德性、功力、才藝的藝術家,並且從功效(善與美)來反復檢驗與完善其功法。
把“功夫”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能够很好地彌補西方哲學因理論理性的偏執而造成的對如實踐、技藝、情感、信仰、修身等的遮蔽。從“功夫”的角度詮釋儒家思想,首先意味著把儒家學說當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夫指導,而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論系統;其次意味著儒家學說的最終目的在於達到藝術人生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對人生作出道德約束;再次意味著儒家經典中的許多言語需要從語用的角度去解讀,而不是祗看字面的意思;最後更意味著儒家經典的內容不祗是“口耳之學”,必須要通過修身實踐才能充分理解。也祗有把所學的知識“體身”化,變成身體的傾向性,才算真“知”。
將儒家學問作為一種功夫體系來解讀,並不等於說它無法從哲學上來理解。恰恰相反,正是通過它的功夫特點,儒家學說的獨特哲學價值可以得到充分顯示。前面所概括的四個方面,都可引出許多哲學上的深刻啟示,在解構有餘建構不足的後現代哲學時代,能够凸顯儒家哲學的建設性價值,彌補西方哲學長期以來對主體本身之修煉轉化的忽略。
功夫的視角確實可以幫助西方學生更容易把握儒家思想的實質。關鍵是它給了學生一個根本啟示,認識到自己面對的不祗是外向的選擇,也要有內在的修煉轉化。西方的人文教育通常稱為“liberal education”,其字面的含義是“自由教育”。這個名稱的一個潛在問題是,容易使人僅僅把自己看作自由意志的主體,接受教育無非是拓寬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功夫視角使他們意識到需要“學以成人”。
中新社記者:在教學和翻譯實踐中,您還有哪些方法幫助西方學生和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
倪培民:西方學生和讀者在理解中國哲學時會有語言和文化上的隔閡。有人因此認為西方人沒法理解中國哲學,這完全不符合事實。西方有不少非常優秀的中國哲學學者。人類有共同的生活體驗和思維能力,這是西方人理解中國哲學的基礎。中國哲學本身就建立在對生活的領悟上。方法對了,會讓這個理解的過程更加順暢。
我的體會是,指出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不同的“功夫”取向,有利於西方人跳出西方主流哲學的框架,按照中國哲學本身的特點來理解中國哲學。這個方法可以稱作“換眼鏡”。一個人不可能不帶任何視角地看問題,就像戴眼鏡,戴上不同的眼鏡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其次是“照鏡子”,就是東西方對比。通過對比可以讓學生看到區別,激發思考。這不僅是教中國哲學的有效方法,我在教西方哲學課程時也會加入中國哲學的內容來幫助學生更清楚地理解他們自己的傳統。比如古希臘把理性思維看作人的本質特徵,而儒家把道德情感看作人的本質特徵,這樣的對比可以對兩方面的理解都更加深入。
另一個有效的方法是“解壓縮”,就是剝繭抽絲地分析、引申,讓文本中蘊含的可能性盡量展開。這對中國傳統經典的閱讀和翻譯尤其必要,因為中國傳統經典中的許多表述非常簡約,而且往往有歧義,但蘊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分析引申中得到許多的啟發。我前幾年發表了一個《論語》的新英譯本,此書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譯文中盡量保留原文中的模糊性,然後在註解中列舉出一些重要的不同解讀,並做一些啟發性的分析引申。
還有一個關鍵的方法是“聯繫實際”——與現實世界的狀況聯繫,與人的實踐生活聯繫,讓學生和讀者認識到他們所學的東西是與現實生活有關的,認識到這樣的學習不祗是增加一點知識,而且是可以得益於此的。我不否認純學術研究的價值,但對一般的西方學生和讀者而言,現實價值是引起他們興趣的根本,更何況中國哲學的許多內容本身就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也是需要在踐行中才能真正理解。
中新社記者:中國哲學如何更好地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倪培民:要更好地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其前提是“聲音”本身的價值。中國哲學要更好地發聲,最根本的就是對中國哲學本身進行梳理,揭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內容,對其做出現代的詮釋。這需要發聲者自己對中國哲學有深刻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做搬運工。
同時,要很好地“發聲”,也需要認真地“傾聽”,瞭解受眾對象的語言和文化背景,能够用對方容易聽懂的語言和方式去介紹。能够在世界上有效地傳播中國哲學的學者,通常是能出入東西古今的。我覺得最有效的傳播途徑是雙向交流,而不是單向輸出。在教學當中,學生學得最好的時候常常是在課堂討論的階段;做學術報告時,給人印象最深的,也往往是在讀完論文以後的問答環節。
其實,在經過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以後,西方哲學很需要有新的建構資源。從交流對話、學習和探討的心態出發,真正與“他者”發生互動、碰撞,中國哲學肯定會成為世界哲學領域的一名要角。與此同時,中國哲學也會迎來自身的現代轉化。(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