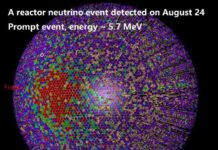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8月1日電 題:一封中國人的信為何成美大學首個漢學系開端?
——專訪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武洹宇
中新社記者 金旭
190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下簡稱“哥大”)校長收到一封來信。信中簡單無他,祗有一句:“先生,我在此寄去一萬兩千美元的支票,作為貴校漢學研究的資助。”落款為“一個中國人:丁龍(Dean Lung)”。
丁龍是誰?為何會向哥大捐款籌建漢學系?他如何能在海外華僑華人遍受排擠的艱難年歲,助力中國文化在西方引起重視和傳播?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武洹宇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是什麼契機讓您開始探尋丁龍的故事?獲得哪些發現?
武洹宇:紀錄片《尋找失蹤103年的“丁龍”》讓我第一次得知哥大的漢學講席是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華工參與倡捐設立。當時正值美國《排華法案》施行期間,這位華工沒有留下中文姓名,人們祗知道他在美國被稱為“Dean Lung”,於是譯作“丁龍”。
我和相關學者及一些民間人士組建團隊,搜集散落在美國多地以及在廣東台山出現的相關史料。我們首先在丁龍雇主卡朋蒂埃捐贈給嶺南大學的通信檔案中,發現與丁龍一起為卡朋蒂埃工作的一名中國厨師馬吉姆(Mah Jim)是廣東台山籍人士,從晚清時期中國人往往是同鄉同族一起出洋來看,我們推斷丁龍很可能是廣東台山籍華僑。而在廣東台山白沙鎮所發現晚清華僑馬萬昌的資料顯示,馬萬昌的字“進隆”,台山話發音與“Dean Lung”極為相近,馬萬昌後人至今保存著1907年卡朋蒂埃致馬萬昌的信件,信中對馬萬昌的稱呼皆為“親愛的Dean Lung”。但馬萬昌是否就是丁龍,目前論證程序還未完全落定。
中新社記者:丁龍所捐出的1.2萬元(美元,下同)在當時是什麼概念?他以“一個中國人”落款,在當時意味著什麼?
武洹宇:1874年,丁龍初到美國,後跟隨卡朋蒂埃,成為其家庭雇員。丁龍捐款後,卡朋蒂埃提議哥倫比亞大學每年從“丁龍漢學基金”的經濟收益中劃撥250至300元保障丁龍生活,進一步證實這1.2萬元確係丁龍個人財產。參考同時期修築太平洋鐵路華工的平均年薪和基礎生活成本,丁龍所捐出的1.2萬元相當于他當時在美國40年左右的生活開支。
在《排華法案》時期,丁龍所踐行的公益,扭轉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也與中國國內的啟迪民智相呼應。“一個中國人”的落款超越傳統血緣、地緣、業緣的特定邊界,轉向一種帶有公益觀念的、面對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現代公益事業,顯然非常特別。
中新社記者:在當時美國排華情緒持續昇溫、旅美華人境遇每況愈下的艱難時期,“丁龍漢學講席”的設立得到了哪些助力?
武洹宇:儘管我們無從得知“丁龍漢學講席”乃至整個漢學系的構想究竟出自丁龍還是卡朋蒂埃,但可以肯定的是,卡朋蒂埃對中國的積極認識離不開與丁龍長達30餘年的相處,而丁龍對至親、宗族及家鄉的深切情感得以轉化為美國首個漢學專項講席,也離不開卡朋蒂埃的慈善興趣。
卡朋蒂埃是當時典型的美國“新富”。他是奧克蘭市的締造者之一,涉足碼頭、電話公司、郵遞公司以及中央太平洋鐵路等多種業務。退休後,他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公益慈善事業,促進家鄉社區發展,推動高等教育,曾為幫助猶太人爭取校董資格與哥大爭執,也力主哥大法學院招收女生……卡朋蒂埃如此熱衷慈善並非偶然,他所生活的時代正處於美國新富試圖通過各種慈善創新,推動社會變革的活躍時期。
因此,哥大漢學講席的捐贈實為兩人基於各自的願景與理念,在彼此交往的情誼和共同認知中相互構成,並將之共同付諸實踐的產物。這種個體的感知和實踐又與當時美國的中國觀產生微妙互動。
19世紀的美國存在兩種中國觀:一種將中國視為野蠻、貧窮與專制的危險之所;另一種則將中國視為文明、富饒與道德的東方聖地,而卡朋蒂埃的中國觀屬於後者。19世紀前30年,中美貿易持續發展,美國民眾熱衷消費瓷器等中國商品,甚至模仿中國風格修築園林,對精緻、詩意、富庶的東方國度的崇尚,成為當時美國家庭對異域風物的嚮往和想象,也激發了美國知識階層對中國的濃厚興趣。
1905年12月的《哥倫比亞大學季刊》中刊登了一封來自卡朋蒂埃的信,信中評價丁龍正直、溫和、恪盡職守,生來就是“孔夫子”的信徒,也自小接受儒教的教育,有著以“孔夫子”和“儒教”符號為中心的想象色彩。此外,我們發現卡朋蒂埃身邊還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因與華人有過直接或間接的接觸而被華僑華人的品性所打動。例如,卡朋蒂埃的商業夥伴、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高管查爾斯·克羅克,他聲稱鐵路的修建之所以能提前完工,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華工所表現出的忠誠與勤勞……可見他身處一個共享著積極中國觀的朋友圈。加之當時開啟中國與東亞研究的設想已經在一些美國大學萌動,最終以“丁龍”之名設立漢學研究的構想在哥大應運而生。
中新社記者:在沒有多少史料留存的情況下,都是哪些人在講述、建構丁龍的故事?其背後有怎樣的文化邏輯?
武洹宇:首先應申明一點,丁龍的故事一開始是基於沒有多少史料留存的叙事,後來進一步演化為關於丁龍的傳奇故事。傳奇故事的建構多少帶有重塑的成分,可分為三個時期,幾乎都發生在美國的“中國熱”與中國知識分子建構自身文化認同的風潮交匯互動之際,是海外中國觀與近現代中國文化主體性叙事交互建構、互相對話的一個動態過程。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義和團運動後清末新政的實施,西方世界認為一個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覺醒中國”正呼之欲出。與此同時,哥大也先後迎來兩位旅華傳教士家庭出身的“丁龍漢學講席”教授博晨光與傅路德,他們查閱與丁龍有關的檔案,將他構建為“孔夫子”的信徒。
第二次發生在二戰時期,勤勞、樸實、堅毅的中國人民形象更新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成為戰時叙述中國的一種主流象徵。1943年《排華法案》廢除,這一時期,哥大校友蔣夢麟將丁龍的故事講述為愛國洗衣工臨終前託付卡朋蒂埃,將積蓄用於有益於中國之事。這是丁龍第一次從被紀念的無聲對象成為具有話語權的“捐贈首倡”與愛國故事的主角,並以樸素平實又極富主見的勞動者形象獲得與日俱增的叙述空間。
第三次在20世紀60年代前後,“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迅速,全球對東亞儒學文化的熱潮豐富了丁龍的形象,將其重塑為“儒家中國”的符號代表,新增以德服人、知恩圖報等情節,既契合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建構需求,也回應了西方對中國的想象與期待。
中新社記者:丁龍的故事能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帶來哪些啟示?
武洹宇:中國學者費孝通曾提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內容”常常會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形式”會上昇為主要的東西。在我看來,丁龍傳奇正是觀察、分析“形式”的最佳題材。
中美學者雖深諳兩國生活與文化的差異,卻仍在丁龍叙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復刻了歷史中想象中國的文化符號。這意味著不同學者所闡述的“中國”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歷史結構所籠罩,是一個多時空不斷對話的動態系統。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國學者和知華友華的外國學者基於對中國的切身認識和情感傾向,擇取其中積極的“中國”符號進行表達,或能引發西方文化乃至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極大善意和興趣。
如今,“丁龍傳奇”迅速傳播,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實踐中被反復講述,融入全球叙事。我們可能需要認識到實踐主體生產文明符號的能動和局限,才能以更加廣博的胸襟和辯證的思維講好中國與世界的故事。(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