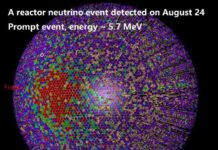中新社香港6月11日電 題:深厚的傳統文化構成我的文化基因——專訪中國當代藝術家徐冰
中新社記者 韓星童
當代藝術家徐冰早前獲委任為香港“文化推廣大使”,在港短暫停留後,趕回意大利為自己新的個展開幕,這也是他近年來著力推動的太空藝術項目的一部分。往日作品所呈現出的前衛性,令徐冰成為最早躋身在國際藝壇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之一,創作足跡遍布全球,浸潤於多元文化之間。
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徐冰坦言,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他的文化基因。這同樣亦是香港的文化底色,他期待以自身的藝術創作經驗與國際網絡,為香港年輕藝術家創造更多展現才華的機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的個展“徐冰:藝術衛星——首部在太空拍攝的動畫影片”4月在威尼斯開幕,這幾年您一直在太空藝術領域深耕,怎麼想到用太空科技這麼酷的概念做藝術的?
徐冰:這次展覽我們設在威尼斯聖塔·維內蘭達教堂。教堂仍在使用中,教堂的白色拱頂很高,我們把在外太空拍攝的動畫影片打在天花板上,慢慢旋轉。地上放了很多懶人椅、休閑軟墊,觀眾可以在地上躺著看。有意思的是,教堂那邊在祈禱和禮拜,這邊好像是一個封閉空間,別有洞天,觀眾躺著仰望星空,整個環境和作品本身同時構成了新的藝術表達法。
這個作品可以說是太空藝術項目的一部分。太空藝術項目是6年前開始的,當時於文德(萬戶創世文化傳媒創始人)找到我,說可以幫助藝術家發射一枚“藝術火箭”。當時我聽了,因為居然能有藝術家的創作可以藉助太空科技,並沒有特別感覺一定要做這件事,因為我不太喜歡那種太高大上的事,還是對現實中身邊的事物有興趣。後來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這個領域是非常值得參與的。
經過各種準備,我們真正發射第一枚“藝術火箭”是在3年前(名為“徐冰天書號”,但發射失敗),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徐冰為什麼要做這個,為什麼要大張旗鼓地搞太空藝術,這樣的東西,有點太不著邊。但我意識到,這是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生長中的空間。這些年掀起“太空熱”,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跟太空科技、外太空的距離越來越近,這一領域的科技和藝術表達的手法、材料等,都有著巨大的變化,可見太空藝術本身的生長性就如此強勁,更不用說未來隨著中國民營太空科技公司的發展,將會帶來更大的生長空間。
中新社記者:您曾多次強調社會現場對創作的重要性,如何從龐雜的社會現場提煉出藝術所需的動力與靈感?
徐冰:我一直對社會現場非常關注,對我來說有太多東西需要反省和表達,這種反省是不斷深化的,不是靈感一來我就可以認識到,也不是一種新的現象出來,我馬上就有反應。
這種現象背後的內部邏輯和更深層的原因,需要慢慢探尋。反映到藝術創作上,這就是一個需要不斷挖掘的課題或項目,在挖掘的過程中,會發現導致這種現象的周邊原因、材料本身也在變異和生長中,這會讓我的創作總是處於一種好像停不下來、沒完沒了狀態中。
作為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比較敏感,那他就會善於摸索到這些現象背後的內部邏輯,這將對人類的認識、思維模式,乃至對這一階段文明走向的判斷,產生新的啟發。
中新社記者:無論是廣為人知的《天書》、與之呼應的《地書》,或是發射“藝術火箭”、用監控視頻剪輯成類型片《蜻蜓之眼》,均呈現出您前衛的創作理念和風格,您一直在嘗試探索創作的邊界和形式?
徐冰:其實不是刻意探索,藝術創作對於邊界和形式的拓展,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使命。我的很多作品並沒有固定的、明確的風格,不像我們概念裡對於當代藝術的定義,要有一種風格、一種流派等。我覺得當代藝術作品本身,並不是當代藝術的實質,實質是當代藝術的思維和態度,這才是當代藝術給所有人、給這個世界提供的有價值的思考方法和生活方法。
我經常說,一個藝術家要保持他的創作活力,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藝術系統本身舊有的知識、藝術系統的既有結構太當回事。如果整天關注某個系統本身的事,你就不太可能有創造力,因為這個系統已經被知識化、系統化了。你的關注應該在藝術系統之外,對社會現場的關注。社會現場不斷變異,而且是無窮無盡的,一個藝術家如果懂得把社會現場的創造力和能量轉化為藝術創作的靈感來源,那他一定是與時俱進的,也一定在永無休止地創造。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希望自己的作品“平易近人”而非“假大空”,怎樣的作品是“平易近人”,藝術又為何應該“平易近人”?
徐冰:我到西方國家參與當代藝術創作後,比較不滿意的部分是西方當代藝術與一般觀眾之間巨大的隔閡和鴻溝。藝術批評用文字解釋藝術,可後來越解釋把觀眾推得越遠。很多作品以一種所謂當代藝術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觀眾嚇跑,或讓觀眾自卑,感覺我不懂藝術,我需要更多的藝術教育,我沒有藝術的感受力。但實際上我們沒有反省當代藝術系統本身的弊病,這造成它與一般人的鴻溝和不可交流性。
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就不太喜歡當代藝術作品自說自話。我當時做過一些作品,比如把畫廊改為學習書法的教室,觀眾可以進入,開始學習書法,然後他們會發現原來這並不是中國書法,雖然它看起來陌生,但實際上是英文,觀眾會覺得很親切。這樣的互動藝術在當時並不多,這是用一種土辦法進行物理接觸上的互動。
現在隨著科技發展,視頻、虛擬現實、感應技術等相繼出現,互動作品變得非常多。但有時儘管我的作品利用了這些高大上的科技,我還是會有意識地隱藏它,希望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簡潔的、日常的、親和的作品。比如《蜻蜓之眼》(該電影用從網上下載的視頻監控畫面剪輯而成),我不想把它做成所謂的實驗電影,我想把它做成一個類型片,講一個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愛情故事,那觀眾看了就會覺得很容易進入。可實際上這個電影本身的前衛性是非常結實和到位的,所以技術的前衛性就可以藏起來,不用特意炫耀。
中新社記者:您在中國求學、執教,後定居紐約,創作足跡遍布全球。很多人覺得,您身上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痕跡與香港的文化特質非常相似。您覺得自己的文化基因是怎樣的?在藝術創作中如何去平衡東方質感與西方表達?
徐冰:我身上的文化基因,是非常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這代人思想成熟的時候趕上改革開放,那時強調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所以我們這代人其實多少都有如何使用西方先進文化的體會和經驗,但卻沒有建立起如何使用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經驗。我們身上的文化基因是複雜的,複雜到了我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我的作品確實涉及多元文化,但我沒有刻意平衡東西方文化的影響,這跟我的生活背景有關,也跟中國有著非常強勁的傳統文化有關,這種傳統文化之強,和在我們每個人基因中埋藏之深、份量之重,對我後來從事及參與國際文化活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國際上工作,個人身上攜帶的文化基因是非常重要的。藝術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國際藝術界關注到,其實就是因為你把你文化中優質的部分,透過你的藝術作品,帶到了國際藝術圈中。當在大的文化環境中,你帶去的東西對調節和彌補那地方的缺失有作用的時候,你的創作就有價值。
中新社記者:早前您獲委任為香港“文化推廣”大使。在您看來,香港文化的底色和優勢是什麼?
徐冰:我算是比較早跟香港文化界藝術界接觸的內地藝術家。最早去香港的時候,我就覺得香港是一個把“藝術為人民”做得非常好的地方,這裡有各種各樣的藝術,歌劇、交響樂、美術館、民間藝術等,不高端,隨處可見,滲透在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中。
香港有非常成熟優質的教育。香港很多藝術家從歐洲學習回來,在香港展開當代藝術創作與實踐,我覺得非常可貴、非常好。
中新社記者:您在獲委任時曾提到,希望能够透過未來的合作計劃和藝術項目,培育香港年輕藝術人才。可否具體談談?在與香港年輕藝術人才的接觸中,您認為他們身上有何優秀特質,有哪些稍為薄弱需要加強?
徐冰:有很多具體的計劃,比如這次我在羅馬美國學院在駐2個月時間,香港派了4個年輕的藝術學生來到羅馬,參與這一新的項目,這祗是一個開始、一個嘗試。
再如“藝術衛星地外駐留項目”,目前開放給全球的藝術家,包括香港年輕藝術家、香港的大學,他們可以參與進來。香港在科技藝術領域還是比較棒的,所以我希望未來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香港年輕藝術家的優秀特質在於他們接受了更全面、更多元的教育,有一定的國際視野,藝術活動有一定的學術支撐,同時又非常努力、認真,責任感非常強,這些都是很好的。香港如今進入新的社會進程,我想這會給他們打開更開闊的藝術視野,也會讓他們對藝術與社會關係的思考比過去有更實質的進展。(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