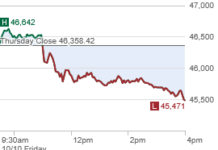女性意識的呈現與女性主體的缺失
——李岑《公號江湖》解讀
鄧麗芝(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15923179186)
女性主義敘事學的主要開創者和領軍人物、美國學者蘇珊·S·蘭瑟,在《虛構的權威》一書中提出敘事聲音的概念。敘事聲音分為作者型、集體型和個人型三種。“作者型”敘事聲音,實際上也就是第三人稱全知型敘事,敘述者“不僅可以自由地展示小說中人物的言語、行為、觀念和情感,而且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愛憎傾向,隨意評點小說中的人物、事件,甚至直接抛頭露面地在作品中發表關於人生、歷史、道德習俗等的各種議論。”[①]李岑的《公號江湖》就是採取第三人稱全知敘事的方式,聚焦在蘇曉藝和孟南暉身上,故事兩條線索交叉進行,江城和慕尼克兩個城市彼此交錯,故事情節跌宕起伏,讀來引人入勝、扣人心弦。
故事以紙媒衰落、自媒體崛起為時代背景,講述了記者蘇曉藝的情感糾葛和事業起伏。小說透過女主角蘇曉藝的視角去看、去聽、去思考,多方面描寫其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刻畫了蘇曉藝這個女性的命運遭遇、價值觀念和心理特徵,這契合了當下關注的性別問題。小說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問題,包括在私人關係和家庭關係中男性與女性的差異和不同,講述了女性對婚姻、愛情、事業的選擇,關照了女性實際的生存狀況。本文根據女性形象、性別意識、敘述方式等理論進行研判,從生育問題、女性形象分析、兩性情感三個方面來分析小說呈現的女性主體性問題。
一.家庭與事業: 從“全職備孕”到重回職場
女主角蘇曉藝是知名報社記者,業務能力強,氣質出眾,盡顯文化人的優雅和品味,丈夫孟南暉是大學教師。張愛玲說,“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子,裡面爬滿了蝨子。”蘇曉藝表面上體面、安穩的生活,實則背後充滿隱忍和苦澀,因為結婚十年沒有生育,她被婆婆和同事諷刺為“不下蛋的雞”。在傳統父權制社會裡,生孩子,成為一位母親,是一個女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一個女人沒有完成生育的義務和責任,她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因為女性有子宮,傳統家庭把生育的責任全部推到女性身上,生育也成為傳統價值觀潛移默化地滲透給女性的自覺擔當。在傳統社會男性凝視的壓力下,蘇曉藝認可作為兒媳、作為妻子的標籤,所以會陷入男權話語帶給她的迷茫和困頓。一向業務精湛、生活獨立的蘇曉藝在生育這個問題上怯場了,她無力反抗周遭世界給她的評論,自己也不自覺地把生孩子當作人生最重要的課題去完成。雖然不能懷孕的責任在男方,但是在社會偏見的壓力下,生育焦慮讓女性迷失自我。蘇曉藝和孟南暉在求醫問藥的同時聽信算命先生的話語,說想要生孩子就要往西邊去。她辭去馬上就升任副總的工作,奔向本來就矛盾重重的丈夫孟南暉,開啟專職生娃的人生之旅。
在事業與生娃發生衝突的時候,蘇曉藝毅然地放棄事業,自覺承擔“延續香火”的責任。因為想要生孩子,蘇曉藝從一個優秀記者,變成一個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完全依賴于男人的女人。西方女性主義者認為,“當母職被視為神話時,就演變成了一種壓迫工具”[②],並且對這種母職神話進行了批判。“傳統家庭結構通過兩種核心方式實現了對女性的壓迫:一是通過男性對女性的家務和兒童照料的無酬勞動剝削,二是通過男性對女性的性和生育的控制。”[③]雖然文本中沒有明確指出孟南暉要求蘇曉藝辭職跟隨他去德國,也沒有表現出兩個人因為懷孕不順利而出現的直接分歧,但是從他們生活和事業的選擇與發展來看,蘇曉藝明顯為生育付出了犧牲事業的代價,而孟南暉按照自己既定人生一路前進,沒有受生育的影響,這就隱性反映出生育責任對女性的潛在剝削和壓迫。
女性被父權結構化成“再生產的工具”,成為“行走的子宮”。蘇曉藝婆婆的形象是封建思想符號的外化,認為女性不過是傳宗接代的工具,具有典型的母職神話思想。她自己把一生都奉獻給家庭和孩子,用自己全部價值去成就家庭的完整,並且以兒子為驕傲,是典型傳統女性形象。在婆婆眼裡,“延續香火”是蘇曉藝作為兒媳婦的本職工作。蘇曉藝與孟南暉結婚多年沒有懷孕,婆婆說“有氣質有品味不會下蛋的女人娶回家有什麼用”,並且勸說兒子跟她離婚再娶。當婆婆得知她懷孕的消息,說“她可是我孟家的大功臣,我要感謝她呢。”當婆婆得知他們離婚之後,說的是“讓她把我的孫子還回來,她走了我不留,但要讓她把我孫子還回來,孟家的根,哪能讓她帶走。”在父權制下,女性被剝離主體身份,只有生孩子的責任,並沒有孩子的所有權。
這個社會處處被封建思想籠罩著,擇偶的標準也遵循著“延續香火”的觀念。故事中的配角,書店老闆、博士生導師老程,和菜刀姐彼此有感情,但是因為菜刀姐患子宮肌瘤喪失了生育功能,老程考慮到自己是程家獨子,為了要給程家延續香火,還是沒有跟她走到一起,而是取了一個年輕二十歲的姑娘,給他生了三個娃。雖然菜刀姐憑著一把菜刀走天下,開了好幾家連鎖店,但在婚戀市場上還是競爭能生育、沒有經濟能力的年輕女性黃丹丹。而實際上,孩子到底給女人帶來了什麼呢?陳落雁的女兒有癲癇,全家將責任推到她身上,以至於她帶著女兒離婚後遠赴德國。因為女兒的疾病,陳落雁被別人認為是一個晦氣的女人,這是社會對一個苦難母親的敵意。蘇曉藝千辛萬苦生的兒子,卻患有孤獨症。更慘的是,陳落雁的女兒小葵在一次公共場合癲癇發作,她用石頭砸向自己,從此成了植物人。孩子是女人一生的牽絆,一個女人成為母親就意味著永遠的責任和負擔。筆者並非提倡女性不婚不育,而是呼籲社會對女性生育的選擇更加寬容和理解,同時對母親這個角色更多的寬容和理解。女性的價值也不只是生育功能,她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生育不只是女性的責任,男性應該與女性共同承擔。
一個女人的價值不應該以婚姻和孩子來衡量,一個女人不只是成為一位母親,一個妻子,更應該成為她自己。當蘇曉藝懷孕之後,她和孟南暉離婚了。離婚之後的蘇曉藝,放棄一切資產,帶著腹中的孩子回國,在無存款、無工作、要養娃的情況下開始創業,這是她離開家庭,走向獨立的開始。女性只有像男性一樣沒有退路、不想依靠他人、奮力拼搏的時候,她的能力和價值才會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女性只有走出家庭,在社會中求生存的時候,她才有底氣走出男權中心話語體系,獲得自身的主體性地位,成為完整、獨立的個體,贏得社會尊重。正如蘇曉藝決定和孟南暉離婚時所說的,“從今以後,請遠離我的生活,不要用你的價值觀來左右我。”從把生孩子作為人生的重心,到離婚、獨自生育孩子、創業,蘇曉藝開始建立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判斷體系。女性只有脫離家庭和生育的規定和束縛,走向職場,獲得經濟獨立,才能獲得自我主體性。
二.女性形象分析:主體性的困境與反抗
性別批評中的女性意識是指,以女性的眼光來洞悉自我,確信自身作為女性的社會存在和生命意義,同時從女性的角度審視外界,以女性的生命特色對這個世界加以理解和把握。當代著名學者樂黛雲認為,“女性意識”包含三個層面:第一是社會層面,從社會階級結構看女性所受的壓迫及其反抗壓迫的覺醒;第二是自然層面,以女性生理特點研究女性自我,如週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經驗;第三是文化層面,以男性為參照,瞭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獨特處境,從女性角度探討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創造的“邊緣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觀,感覺方式和敘事方法。[④]《公號江湖》中“女性意識”,體現在作者對女性命運遭遇、價值觀念和心理特徵的刻畫和呈現。
蘇曉藝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審美都具有小資情調。“所謂的小資情調,是指一種獨特的審美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格調,表現為刻意追求精緻高雅的生活品位,講求生活細節,善於營造浪漫氣息,追求休閒享受,精神上標榜自我,張揚個性自由,帶有自閉自戀式的孤芳自賞等特徵。”[⑤]蘇曉藝生活體面自在,待人接物友好良善,情感豐富細膩。作為一名女性,她是喜歡自己的女性特質的。作者多次刻畫蘇曉藝作為女性的穿著打扮和心理特點,她在見李無言時,不斷地審視自己的衣著和妝容,連衣裙、香水、手鏈、撲粉補妝等等。如果李無言時一面鏡子,她想在這個鏡子前展現的是自己的女性特質。如果李無言是一名觀眾,她想讓他看到的是她作為女性的美。蘇曉藝和安硯見面,“兩人習慣性地打量對方一下,把對方的胖瘦、膚色、衣著服飾互相點評一番,然後才落座。”[⑥]被蘇曉藝當作楷模的同事趙主編,“氣質高雅,也是個典型的香水控服飾控旅行控,她們之間堪稱情投意合”[⑦]。描繪女性形象,突出女性特質,這是看見並尊重女性的表現。但是蘇曉藝對於自己這種溫柔的女性外表是有一絲自戀情結的,與她的業務能力一樣,更多的是通過作者的敘述來表現她的優越,這種優越是一種底色。蘇曉藝的女性特質下的內心是矛盾而複雜的,波伏娃說得好,“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絕佳的外貌對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種武器,一面旗幟,一種防禦,一封推薦信。”[⑧]蘇曉藝就是這種漂亮女性,光鮮亮麗的外表是她的有力武器。
蕾切爾·卡斯克說:“我如何理解‘女性’這個詞呢?虛假的事物;是化妝品的儲藏室,是充滿了灑了香水的精品店以及包裝精美的商品的世界,也是充滿了假睫毛、法國潤膚霜、粉末胭脂的世界;是受苦、自控、忍耐等字眼通常只與減肥相關的世界;是充滿溫和、自願壓迫的世界……”[⑨]蘇曉藝在女性特質自戀的外表下,有著身份認同危機,這種身份認同讓她“充滿溫和”、“自願壓迫”。
女性主義強調女性身份的差異性與多變性,主張女性要處理好自己與社會、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當女性無法正確處理這些關係時,便會偏離對自我的正確認知,從而出現身份認同危機。女性的身份認同危機在於難以妥善處理自己與社會、自己與他人的關係,這兩重維度中蘊含著女性被社會施加的身份表徵以及被賦予的個人符號呈現。蘇曉藝的同事、也是她的對手,盛希莉諷刺蘇曉藝是“不下蛋的雞”,蘇曉藝感覺被戳到痛處,被激怒到去找她理論,痛哭流淚,她對於外界給她的標籤充滿委屈,但也慢慢自我解脫,“不下蛋就不下蛋,下不了蛋就不下蛋,人生哪能事事順遂事事完美?!”[⑩]蘇曉藝作為妻子,她的母親身份得不到實現,則被婆婆嫌棄,在單位也被揶揄“沒有孩子的好處”。她自己也知道不能懷孕不是她的問題,但是當外界所有人都把“錯誤”指向她時,她不自覺地接受了這樣的標籤。“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那麼家庭語境下的語言能指符號所施加給女性的就是詢喚關係的總和,構建出一個由身份、地位、名號所共同組成的物件,這便是社會賦予女性的身份。”[11]女性被社會施加的身份所桎梏。
優雅得體的蘇曉藝骨子裡其實是一個沒有力量的人。蘇曉藝第一步錯就錯在為了追隨愛人去德國而放棄了自己擅長的工作。在毫無準備的前提下,她放棄國內即將升任副總的職務,毅然投靠在德國訪學的愛人。蘇曉藝做出這樣的選擇是軟弱的,她在婚姻中明顯感受到了丈夫的專斷和自私,生不出孩子也不是她的錯,但是她仍然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蘇曉藝辭職的時候一往無前不計後果,離婚的時候同樣是這種“傻白甜”人設。婚姻中,她在沒有明顯錯誤的情況下選擇淨身出戶,而且是在她自己懷有身孕的情況下。一個沒有工作、離婚、肚子裡還懷著孩子的高齡女人,生活會有多艱苦,她是沒有腦筋去考慮的。這個決定也為結局埋下伏筆。蘇曉藝是一個從來不為明天著想的理想主義者,孤勇和孤傲有餘,缺乏應對現實的真實能力。
蘇曉藝這個主角美麗善良,卻是“戀愛腦”(下文具體分析),外表和精神上都表現出自戀傾向。而小說中的兩個配角更具備現代獨立女性的特質。陳落雁像孟南暉一樣,是山區工廠子弟,通過自己的努力,一路碩博,到德國做訪問學者並且留在了德國。陳落雁漂亮、性感、嫵媚,而且聰明、勤奮、獨立,德語和英語都非常好。她的生活並不輕鬆優越,一個人帶著患有癲癇的女兒在異國他鄉,自己面對一切困難。但是她從不向生活低頭,保持著靚麗的外表和堅強獨立自由的個性。她非常務實,但也有情有義,為了留在德國,她與一個年紀大的德國人協議結婚,得知老頭病情嚴重精神崩潰的時候,她盡其所能地幫助他安撫他。在陳落雁的世界裡,感情是第二位的,生存才是第一,自己的感受才是第一。她的選擇不需要別人來肯定或者推動,她不束縛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束縛。她愛上孟南暉,但是她不依附他,也不限制他,他們獨立自由,靈魂相惜。她說“何苦想那麼多,肉體是用來享受的。”[12]這看似離經叛道的言論背後,實則顯示了陳落雁有很強的主體性,她的身體屬於她自己,不被傳統道德所束縛,這是女性正視自身的欲望,將自己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脫離男性凝視和規訓的束縛。
安硯也是一個獨立女性,她從一家跨國公司的醫藥代表做到大區經理,開著路虎,住著高檔社區。正如她說的,“與眾不同的背後,是無比寂寞的勤奮,要麼是血,要麼是汗,要麼是大把大把的曼妙青春好時光。你看到我光鮮的一面,卻沒有看到我風裡來雨裡去。”[13]辛勤工作,在職場上一路高歌猛進。安硯在感情上也十分清醒,他認為愛情和婚姻是靠不住的,對愛情和婚姻沒有幻想,她說:感情只是生活的小調料,不能當飯吃。安硯認為,愛情婚姻是建立在兩個人共同進步的基礎之上的,她自己內外兼修,保持身材、苦練本領,而她的老公不進反退,他們的婚姻就自然而然走向破裂了。她和情人江洪波兩情相悅,也相互利用,曖昧不出界。
相比安硯,蘇曉藝有掌控生活的能力,但沒有掌控的意識。她捨棄事業追隨老公生孩子,很難說是主動的還是被逼的;她和孟南暉離婚,懷著孕自己獨自回國,主動放棄本該屬於她自己的財產。這些選擇都是失去自我的表現。表面上看蘇曉藝文藝、有文化有情調,但在現實生活的泥濘中,蘇曉藝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有著林黛玉式的純粹與脆弱。從蘇曉藝和安硯的比較發現,女人只要不沉迷於愛情,不感情用事,就會把時間精力用在正確的事情上,表現就聰明很多。
三、兩性情感:依附無望與空洞曖昧
因為個人抱負受制於女性身份和社會壓力的阻礙,女性“仍然在生活中騰出一個位置給予男人和愛情”。[14]沉溺於內在性的女性把愛情當作生活本身,但從小就被教育有超越性的男性只把愛情當作一種消遣,女性一旦深陷這種空洞、沒有回應的兩性關係中,自我虛無化的同時,內在性的處境也更加艱難。蘇曉藝就是這樣沉溺於感情的虛無中。男性在兩性關係中支配女性並情感善變,是女性不可靠的脆弱支柱。
蘇曉藝與孟南暉作為夫妻,無論是外表還是職業,或者是能力上都是旗鼓相當,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從性愛姿勢到生活安排,孟南暉是他們兩性關係中的主導者,蘇曉藝明顯是處於被“壓迫”的一方。他們沒有生育問題出在孟南暉,但是他還是默認外界對蘇曉藝的指責,不願主動承擔責任。生活細節上的分歧,都是以蘇曉藝的遷就和妥協來處理。到了德國,孟南暉很快出軌陳落雁,但與蘇曉藝離婚時,他卻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要求夫妻共同財產全部歸自己所有。如果孟南暉對蘇曉藝情深意切,他們的婚姻和諧幸福,或許可以說蘇曉藝放棄事業選擇家庭,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婚姻千瘡百孔、暗流湧動。女人啊,你不顧一切奔赴的愛情和婚姻,等待你的是什麼呢?顯然,在蘇曉藝的婚姻中,兩個人的天平是不平衡的。愛情需要激情,但是婚姻不需要,婚姻需要的是齊頭並進、相互妥協。
如果說孟南暉對她意味著婚姻的殘酷,那麼李無言對她意味的就是愛情的幻滅。“愛”是對“忠誠”的超越,它能瓦解一切虛偽的忠誠和隱秘的自欺,真正的愛忠於那奇跡般的偶然性。生活裡很苦的人,給她一絲甜就能填滿,像蘇曉藝這樣的女人就是容易被深情和苦情打動。或許李無言才是與蘇曉藝情投意合的那類人,他們都喜歡文字,彼此之間“深度誘惑”,對生活有一種別樣的希望。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在《愛的多重奏》裡將愛情稱作是“小型的共產主義”,在愛情中雙方都得到至高無上的承認,在李無言面前蘇曉藝感受到了被尊重被欣賞被愛的感覺,她迷戀于李無言給她的初戀般的戀愛感覺。蘇曉藝與李無言的愛情,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真實動人,這實際上是女性最喜歡的“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戲碼。有錢不過是李無言身上不值一提的優點,重要的是他儒雅紳士、品味不俗、鐵血柔情、偏偏對你一往情深。這種男人、這種愛情,就像故事情節一樣,只是蘇曉藝生活的一個插曲,一個偶然事件。但是這個偶然事件已經給她的生活帶來了震驚的效果。情感是複雜的,道德標準有時與人性背道而馳,那些忠於自我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愛奮不顧身的人是純潔的。如果說和孟南暉的婚姻是傳統社會中的圍城,蘇曉藝的一進一出,足以體現女性在兩性關係中中的弱勢地位。那麼與李無言的愛情,就像夢境一場,異常絢爛美好,卻不切實際,夢醒之後只剩無盡的惆悵。一個中年女性最可貴同時也是最愚蠢的是相信愛情,把愛情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面對愛情,蘇曉藝是勇敢的,甚至是“戀愛腦”。在得知李無言突然失去聯繫是因為牽連到一個貪腐案件時,她離婚回國,在自己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到處找人説明他打聽情況。而事實上他們的關係並沒有公開,她對於李無言並沒有合法的位置。正如書中多處出現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愛是第幾個字?”[15]愛情對於現實生活而言,是奢侈品。李無言的消失,意味著愛情的幻滅,他與蘇曉藝之間所謂的刻骨銘心的愛情也不過是空洞的曖昧。
對於蘇曉藝這樣的女人,李無言這樣的男人幾乎滿足了她對於愛情的一切浪漫幻想。在更深刻的愛情面前,她沒有愛的能力。德國男孩費恩,對蘇曉藝的愛讓他穿越生死,穿越千山萬水奔赴中國,來到蘇曉藝的身邊,想要和她一起生活下去。面對這樣深刻的愛慕和欣賞,蘇曉藝並沒有全然接受。費恩的母親不同意他們在一起,在費恩因為母親病重需要回國的時候,蘇曉藝也沒有揭穿真相,而是讓他離開。愛情是難的,需要克服種種困難和阻礙,蘇曉藝沒有勇氣去衝破費恩母親的阻礙,這種阻礙象徵世俗和封建思想。因為她和費恩之間年齡相差6歲,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費恩母親的反對,蘇曉藝再次在兩性關係中敗下陣來。在兩性關係中,蘇曉藝是一個沒有主體性的人。一個有主體性的人一定是一個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人,一定是一個不滿足於被禁錮在婚姻中妥協于男人的人,一定是一個不沉溺於愛情幻想的人。
蘇曉藝人生中的困境都是依靠同性朋友的幫助走出來的。當李無言突然從她的生活中消失的時候,她內心非常焦躁和痛苦,這時是好朋友安現在給她提供消息和幫他分析情況,幫她走出情感的漩渦。當蘇曉藝隻身回國,有孕在身又無工作的時候,又是安現在幫她提供人力物力幫助。最後,她創業失敗、房子被前夫要回去、另一個愛她的人即將離去、兒子自閉症,生活落入低潮。唯一永遠不變的是安現這個朋友一直在身邊。女人之間的懂得和欣賞遠比婚姻愛情更可靠。
四.結語
蘇曉藝作為一個現代都市職業女性,對她的刻畫主要體現在情感偏好和精神追求上,她的人生選擇和價值取向透露出現代語境下女性的身份認同危機。作者所塑造的女主角成長之路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情感的幻滅下,獲得自身的完整性依靠的是具有雄雌特徵的性格特點和女性朋友的幫助,而不是借助男性的力量,也不是在情感中找到歸宿,更不是回歸家庭,這是現代女性的真實寫照。
在現代都市文化和社會語境下,女性要想在世界關係和生命內在性的超越中獲得自身的主體性地位,就要在經驗世界中建立自我意識,塑造自己,無論最後是在家庭生活中獲得世俗的幸福,還是在職場上闖出一片天地,只要是對自身從屬地位的覺醒和反叛,價值追求是自由和多元的。對於一個獨立女性,婚姻愛情和事業,一切都應該是以自身價值的實現為前提。蘇曉藝,在事業與生育之間選擇生育,在婚姻與愛情之間選擇愛情,在物質與精神之間選擇精神,最後失去感情、創業失敗、孩子自閉,她的生活面臨再一次的重新出發,可能充滿無限可能,但是面對的困難也可想而知,所以蘇曉藝最終的自我覺醒和成長的力量還不夠。如果小說以女性自我經驗為本,將女性角色的自我關注擴大到對女性自我成長之路的關注,塑造一個獨立強大的女性形象,小說的感染力會更強。
[①] 高小弘:李锐小说叙事声音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34页。
[②] 吴小英: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变革、争议与启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20-29页。
[③] 吴小英: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变革、争议与启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22页。
[④] 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文学自由谈》,1991 年,第 3 期。
[⑤] 袁梅:《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小资”和“小资情调”》,《齐鲁学刊》,2005(05),第90页。
[⑥] 李岑:《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6-97页。
[⑦] 李岑:《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8页。
[⑧]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舒小菲译,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72页。
[⑨] [韩]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黄建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⑩] 李岑:《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3页。
[11] 王大六、朱旭辉:《女性意识重构的真实呈现——评电视剧<加油!妈妈>》,《当代电视》,2023第1期,第47页。
[12] 李岑:《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08页。
[13] 李岑:《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6页。
[14]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15] 李岑:《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