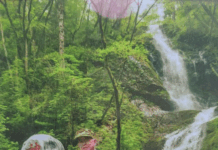作者:郑建国
“校长,我们现在可否把那大的横幅拉出来?我们看好了,就在院门口两边,两人一条?”此刻,被喊作“校长”的老郑,正在上海某区的一法院审判庭里,参加一“共有财产纠纷案”的开庭活动。此刻,他耳听着那年轻女法官与坐自己边上的M律师,就原告律师起诉词中的个别细节所作的一问一答式的对话;眼睛,却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些文字。老郑晓得,上述文字中提及的横幅,是他与朋友为此次官司所准备得两幅横幅之一,组成它的两条内容是“坚决彻底铲除国徽下面的黑恶势力” ,“强烈要求撤销(2018)沪0106民再一号判决”。由于今天是关于此案的首次开庭,主要就是由原告律师宣读起诉状,被告律师则作反驳辩护,并就案中涉及的一些事实予以沟通确认;由于作为原告方的老郑两嫡亲姐妹都没有出席,老郑原先准备的一通直斥对方犯有偷盗不孝不仁不义罪的慷慨陈辞,一下子失去了泼洒的必要,不免令他有泄气之感……所以庭上气氛显得有点平和,甚至还带有股此类场合难得的一种松散的意味。
说实话,眼前的这官司,就是老郑这些年的浑身毛病满腔怨恨的渊源。当六年前他那两个同胞姐妹发起第一场要求分割父母留下的房产诉讼之初,他是根本不以为然的。心想我生在这长在这结婚生女都在这。父亲虽是一位38年入伍的八路军老战士,可骨子里仍是个重男轻女传统思想浓厚的农民,他和母亲就我一个儿子,满心指望我为他们两老及另位身心俱残的大女儿送终。所以这里的房产证上就只有他俩和老郑及他残废姐姐四人。而那两位健康姐妹,父母也没亏待她们。在两人结婚时,分别给她们一人一套组织增配的房子,当然户口也一并从这里迁了出去。老郑父母的用心,他们的这些安排,街坊邻居、老郑父母的战友等都是知道的,根本没有什么疑问或争议,包括两姐妹,也没敢有什么声音。当然她们也因此心安理得的认为老郑作为儿子与父母住在一起,照顾老人是自然的,没她们什么事。母亲去世后,父亲老年痴呆症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生活已逐步完全不能自理了。于是老郑白天工作再忙再累,下班一回到家就得配合保姆为老人换尿布等。夜半,哪怕天再冷的时候,只要保姆一呼唤,便立刻起身和保姆一起为父亲去清洁身体。偶尔因公出差不在家或晚上晚回来,也预先安排好同事或朋友来家里,帮保姆替老父整治好尿布等让他睡下方才离去。像此刻发信息询问是否可以拉横幅的金老师,也比两姐妹中的任一人,更多的照顾过老郑父亲。父亲去世后没几年,两姐妹提起了要求继承父母遗产也就是房产的诉讼。也就是在这座法院里,当时审理此案的Y 法官颇为同情地对老郑说,因为你父母未留下任何遗瞩所以按照我国有关法律,你现在住着的房子那两姐妹也有份。最后判决是:老郑与一直住院治疗的残疾姐姐,各获得40%房产,那两姐妹,则每人各获房产的10%。对这判决给那两姐妹一块,老郑虽不满意,但考虑到此时残废姐姐还在住院,大家还要团结起来一起照顾好这姐姐,所以默默地接受了这判决。残疾姐姐住院治疗了前后共达八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老郑只要人在上海,就每天必去姐姐医院看望一下。再忙再累,哪怕在姐姐病床前只能待一会儿,握一下手,老郑也乐此不疲。有时人不在上海,老郑仍会请同事朋友,代自己去看望下姐姐。老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这苦命的姐姐,每天都能感受到亲情的存在,在她那个世界里,不要感觉孤独寂寞。至于那两姐妹,妹妹则还能一个月去看两三次,而那姐姐,则数月方去一次。就这样,老郑这位原本被街道家庭医生,认定活不到60岁的姐姐,最终阳寿近70了。在住院八年多的时间里,凡关于姐姐治疗等相关的问题,都是由老郑出面与医护人员协调解决的。及至姐姐离世时,始终陪在姐姐身边的,也只有他一个亲人。可就在不久该姐姐骨灰落葬活动刚结束,老郑等还在陵园墓道上时,两姐妹中大的那位,便迎上来一脸认真地对他说,“维新(残疾姐姐名)的40%你考虑过吗”?“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老郑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冷冷甩出这句话后就径直朝前走了……没过多久,老郑收到了法院关于残疾姐姐遗产继承的诉讼传票。再以后,老郑山东老家同父异母兄姐后人,闻讯也杀入要求继承房产的战团。面对这种情况,法院后将对父母、残疾姐姐遗产继承的所有诉讼要求,合并为一个案件来审。期间经历了撤销前一个诉讼判决、主审法官易人等事件。在这期间,两姐妹中那大的四出活动,出现了一连串的骚动作,终将原先一开始主审此案,看似对老郑比较友善对老郑遭遇比较同情的美女X法官,在以后判决作出之前2个月都不到的某天,突然调换成与老郑这位姐姐有关系的有容嬷嬷作派的G法官。果然,该法官主审后,不论是法庭调查、私下沟通等,明显的是站在两姐妹这一边:譬如认为,她们当初从父母那得到的婚房是赠予,是不同于老郑从父母那得到的房子……两姐妹出于私利,默认乡下那帮亲戚对父母的攻击,以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父母的照顾……他们串通一气合为一股。所以当时自辩的老郑,面对的是这几股势力。而G法官与那位同某部著名抗日电影中伪军司令同姓同相的书记员,在临判决下来不久前的沟通时,为使老郑同意不再追究母亲去世后负责家里管账的妹妹,存在严重的财务不清的问题时,两人一起劝诱老郑在同意不再追究那问题的沟通记录上签字说,“钱款算下来相差并不大。其实,你房产上多一点早就有了……”最终判决书是快递送到家的。上面房产是这么分割的:老郑是50%,乡下亲戚分到7%,而那两姐妹则得到了43%,竟然达到总房产的一半快了。法庭对那么多证明其父母本意是现住房留给老郑、老郑夫妇是如何竭尽全力照顾父母及残废姐姐的材料,那些来自街坊邻居、上海亲戚、父亲战友家人以及医院医护人员的大量证辞证言,根本熟视无睹。对此,老郑当然不服强烈不满。
在随后一年里,老郑先后向市二中院、检察院提出上诉和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审判中的问题等,可事实证明想推翻人脉深厚的G法官作出的判决,真比登天还难,老郑后来分别得到的是“维持原判”、不予介入的答复。老郑仍未气馁,又走上了信访之路,开始通过信访办给市领导写鸣冤信。尽管信访办也曾回信回电,称来信要求虽非他们权限所能办的(即不能送呈领导一阅),但已将信转或抄示给市高院了。所以多少还是给老郑留下了点希望。
“郑某某”,女法官的一声招呼,把老郑一下子从回忆中又拉回到眼下。“你住在这房子里多少时候了?”,“从出生到现在,60多年了,始终在这里”!老郑缓缓地回答,末句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可从信访办最后一个来电过去几个月了,没等到高院任何一动作信息。倒是在距这次开庭三个月前,这家区法院送来了两姐妹把老郑告上了的诉讼传票。在一起过来的起诉状里,老郑看到自己已被冠上了“霸占房产”的罪名,被要求按市繁华地段房屋租赁价格,赔付她们一直没拿到上次判决给自己那比例房产的所谓损失。老郑知道,这是两姐妹在逼迫自己卖房子,她们有数老郑只是个一年拿十万出头点退休金的公务员,若她们胜诉,老郑除了卖房交付她们按那判决份额房产的现金外,别无他途。可老郑更铁了心,房子是无论如何不同意卖的。倒不是这套年代久远设施陈旧墙壁斑驳的房子,除了坐落在上海一条著名商业街之外,其它还有什么好的。促使老郑这么做的关键是,老屋由他继承住下去是父母的本意,他也践行了为残疾姐姐照顾送终的承诺。重要的是,老屋他住了一辈子,这里的每寸地上每个角落,都留有父母、苦命的残疾姐姐他们的气息,保存着关于他们的所有记忆。每每想到这场官司的前景,老郑耳畔似总会回响起过去某部电影里的一句著名台词,“老子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虽说这话有点粗糙极端,可老郑结合自己的情况想想也是的:自己就这一套房,哪像两姐妹,各有两三套房。反正自己已年近七十,来日也无多了。虽做不到鲁迅所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我以我血荐家园”还是能做到的。对老郑的遭遇,他众多的友朋是非常同情的,对那不公正判决,及背后腐败分子那黒恶的力量,都持反对谴责的态度,支持老郑继续上告,继续鸣不平。此次听说老郑有这官司,有这么个开庭,便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想以旁听的方式表示声援。可谁知法院到时却以“疫情期间,避免交叉感染”为由,只允许给两个旁听名额。后经M律师交涉,总算临时又增加两个名额。
此刻手机又是一阵震动,屏幕上跳出了几行字,“校长,戚教授刚在问,是否可叫他那某国领事馆负责文化交流的侄女过来了?”趁着现在法官正和辩控双方律师就一些事实予以确认之际,老郑迅速地发去“等一等,听我的”这几个字。此后直到开庭结束,老郑始终没同意把横幅拉出来。
开庭结束众人散后,老郑在同法官作个别沟通之时,意外获知妹妹今天没来,是因突患脑梗。闻听此讯的老郑浑身一震,于是又折回审判厅,唤住正准备离开的控方B律师。在请对方转达其委托人必须尽快归还窃去的房产证部分补偿款的要求同时,务必代向妹妹转致自己希望她尽快痊愈的祝福。对这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当时社会、家庭变化而曾有过一段相依为命共同经历的妹妹,老郑始终有着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此时,老郑不禁忆起妹妹所住的那小区一邻居的信。那邻居是通过一朋友认识的。当时他了解了老郑与他姐妹的关系后,很是义愤填膺,自告奋勇地说要以大楼居民的名义写信斥责下那妹妹。后朋友还真转来那邻居信的草稿,称让老郑把把关。老郑想起就在前两天,才刚刚交还详细修改过的那封信。该信的主要内容记得是这样的,“601室的住户,我是某某大楼的居民,今听你哥哥同事的介绍,我们整幢大楼的人都觉得很没面子:没想到我们居然有你这样的邻居!70年代末的某天深夜,在你父母因病不能、而你一张床上的姐姐又装睡不肯送正频繁腹泻的你去挂急诊的情况下,就是你哥哥推着自行车送你去医院就诊的(你父母当时着急的是就在前几天,弄堂口31号一邵姓70届女孩就因菌痢去世——自注)……2001年,又是你哥哥,帮你那去年刚做了父亲现住楼上1104室的儿子,摆脱了在原校不学好要留级的窘境,让他在自己做校长的学校里插班就读,并派优秀负责的老师,予以重点关照……最终,考上了高中;后又安排从民办到公办去借读……你儿子终于学好走上了正轨。象这样大的忙,你哥哥都帮了,可你又是怎样回应的?我们不说图报,知恩是最起码的吧?可你不仅忘恩负义,更是恩将仇报:与你那蛇蝎心肠一心想报复父母当年不让未婚先孕想结婚在家而遭拒的姐姐狼狈为奸,与骂你父亲是“陈世美”的那帮乡下不肖子孙沆瀣一气,狠狠地在明知父母是給哥哥的房产上咬了一口……松口吧,要么,走吧,去你那幢交通路的房子待着吧”!
妹妹的病应该和这信没关系吧?可又忆起:刚来的路上,朋友还说那邻居称赞老郑改得好,说过几天会尽快把信发出去的……这么一想,老郑纠紧的心,略微放松一点了。
当老郑、M律师以及作为旁听人员的一债务清理服务公司的老总等,最后出现在法院大门口时,外面正等候的一干友朋便呼啦啦地拥上来了,七嘴八舌地询问开庭情况。在前往停车场的路上,老郑努力告诉大家,今天的开庭,只是对方宣读了下起诉状,我方则作了不同意指控的辩护,其余一般性地了解核对了些情况,更加激烈复杂的法庭斗争还在后面。这时一位退休前是老郑同一系统的朋友叫道,“有这么复杂吗?老郑,你不是担任过一全国性学术组织的副职,好赖也算是一民间副国级干部了,他们敢乱判吗”?还未等老郑接口,旁边的朋友便纷纷说道,“没用的,民间的根本没用”!“这些有点黑恶关系的公检法人员,只要对己有利没什么敢不敢的……”
这时一在虹桥开发区工作的台籍企业家挤上前说,“老郑,我得说,你那官司的判决实在太不公平了。在我们那里,这样荒唐的的东西是不会出来的。即使被你们这儿骂得一榻胡涂的蔡英文总统,虽是女流之辈,可在对待有民愤民冤的事上,是绝不含糊的。她甚至会亲力亲为,亲自倾听……刚在路边等你时听你老同学介绍,你还给市主要长官写过信,却一直没有得到答理,有这么傲慢吗?还有,听说你们今天还带了写有诉求的布条准备展示出来,怎后来不见下文?”这次老郑没让其他人接口,直接就对这位叫大强的朋友说道,“噢,不能这么说!你们那蔡姓女人管多大地方多少事,和我们这里的能比吗?信我是给市领导写了,大家还劝我继续往上写。朋友们还告诉我就我参加的那研究会中,有人认识京城某小学家长委员会一成员。那爷爷辈的家长与总书记是陕北一起插队时的室友,称做一个上达天听的信使是没有问题的……可想想现在正是抗疫紧要关头,从电视里看到的那位领导包括总理总书记的神态,都是很有点疲惫的样子,我是能理解那不答理,更不忍心让中央领导为我这点事花费时间和精力。从刚才开庭及法官的表现来看,我逐步觉得没必要采取拉横幅这样的举动,给领导们添堵添乱……我可以等待。我可以等他们忙过这阵再来关注我这事……”回去的路上,看着走在前面的金老师与来时一样,仍背着那鼓囊囊的双肩包,想起内中还有一幅写着“昔日公务员,今天怨民一”小一点的横幅,耳中似响起一首小时广为传唱的歌曲《我是一个黑孩子》那熟悉的旋律,并依稀记得那句颇切合自己此刻对等待前景感到缺乏信心心情的歌词,“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老郑此时急切地往前赶了两步,边走边想:希望一切会好的,希望金老师双肩包里的那两幅横幅,以后绝不会如朋友所说,最终还是得出现在金水桥前大会堂外纪念堂里东交民巷那儿……
【作者简介】

郑建国,1955年生于上海。1972年进上海导航仪器厂务工,做过钳工电工。1979年在恢复高考的第三年,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进入上海普陀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执教初中语文。在该校先后担任过教导处副主任、副校长、校长。2006年开始,到该区教育局任副局长,直到2015年退休。2014年,他还曾担任首届中国教育学会美育研究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在他长期的教学实践与教育管理的工作中,曾与人合作编著过十来本关于教育、读书励志方面的书。退休前后,开始在诗歌小说创作上作了点尝试,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作品。